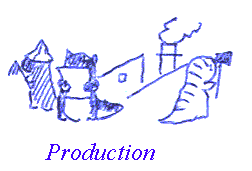
馬克思主義談生產:直接勞動產生剩餘價值
二戰之後的新經濟:知識產生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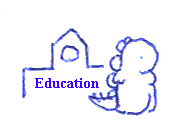 |
 |
 |
新型態的生產過程與問題
˙就業與人生
˙知識生產與實際操作的落差 (知識的變容性與技術操作的單調)
˙後泰勒主義的生產 (知識與技術建立的長期訓練與技術流變的快速)
資訊時代的誕生
羅耀宗譯,意外的電腦王國(聯經,1994)
1970s 微處理器Invention到Development的時代
全錄PARC的工程科技研發---卡在完美的Invention,走不下去
1980s 日本傾銷的危機時代
1980 Apple III上市導致IBM的Open architecture式的PC發展
IBM的BIOS
Intel的8088微處理器
Microsoft的BASIC
PARC的CM/P 莫名其妙的交易失敗,Ms搶下QDOS取代之,獨占軟體開發
1982 Compaq反向拆解BIOS,相容電腦侵占整個市場,IBM整個沒搞頭 (幾千億美元的錯誤,只有這一次)
1984 Macintosh發展成功,PC市場成形
1987 IBM大反撲
1. 發展作業系統OS/2以取代DOS
2. MCA新匯流排以獨占一片混亂的PC市場 → EISA新匯流排聯盟的反抗
整個失敗!!
1996 Ms發展Windos 3.0上市 微軟王國正式形成
定位:新經濟
Fred Block & Larry Hirschhorn, New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 Postindustrial Perspective: Revising State
The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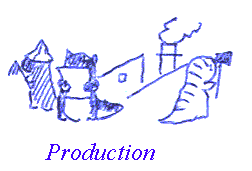 |
馬克思主義談生產:直接勞動產生剩餘價值 二戰之後的新經濟:知識產生價值
新型態的生產過程與問題 |
高科技產業的空間群落
Saxenian, A. (1994). “Lessons from Silicon Valley.” Technology Review, 97(5):
42-51.
Kvamme, E. Floyd. (2000). “Life in Silicon Valley: A First-Hand View of the
Regions Growth,” in The Silicon Valley Edge, pp. 59-80.
Lee, Chong-Moon et al. (2000). “The Silicon Valley Habitat,” in The Silicon
Valley Edge, pp. 1-15.
新經濟的特質
Seely, John Brown and Duguid, Paul (2000). “Mysteries of the Region: Knowledge
Dynamics in Silicon Valley,” in The Silicon Valley Edge, pp. 16-39.
※Marshall, A. (1919). Industry and Trade. London: Macmillan. Pp. 269-88.
世紀末科技怪物:Silicon Vally & Science-based Industrial Park / 竹科
高雄加工出口區
第三義大利的手工紡織
十九世紀的英國 --- Marshall看聚落式產業
|
曰:Why clustered?
|
1. 市場外部性效應 / External Economics ˙共享基礎設施 2. 產業氛圍 / Industrial Atmosphere 曰:通訊技術進步會消滅clusters |
一、 理論回顧
簡單的展開產業聚落的議題,當Marshall的"通訊進步會消滅產業的聚落型態"理論被歷史推翻的時候,我們才可以從這個古典經濟學犯下的小錯誤,發現我們身歷其境都無法體認的知識特質。
J. S. Brown直接的反駁了許多針對網絡通訊進步打破科技傳播界限理論,強調知識的地域保固性,以及由這個知識的地域保固性,從而畫下的地理界線,畫下了產業聚落成功的路標。
簡單的統整這個觀念,我們可以窺見知識的動態特性。知識的兩個動作便是固守與窺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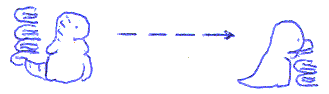
在F. Block和L. Hirschhorn討論後工業社會的新生產力:知識 的時候,相當程度的使用了個人(或勞工)接受之事後的capacity這個字眼。他們在該文章中論述後工業社會的知識經濟化產生的社會問題,除了破壞工作就業對人生規劃的意義外,也講出了在尚未隨著知識與技術進步的生產管理組織底下,高知識或高技術價值的勞工所面臨的高流變性技術就業所產生的矛盾;套句現在念工科的學生常說的一句話:「我現在學的東西頂多只能賺這幾年錢,要賺就要快!」兩位作者認為滯步不前的生產管理組織,會造成對高知識技術勞工所有knowledge capacity的浪費,從而使這些勞工質疑起學習這些知識的意義感與價值。透過和這後工業社會理論的對話,我們可以看見知識的價值,並不在於現有的生產過程本身。透過互相固守與窺探知識技術的產業聚落,展現的特性絕對不是在那些既有有搞頭的事業一窩蜂的大賺一票;相反的,個人對知識的capacity,不在於區區的累積資訊、或是將之投注到生產過程上,而是要將知識用來改變生產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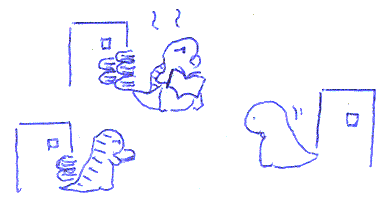
也就是說,在產業聚落裡,產業們藉由聚集所畫下的知識流動範圍裡,他們不但是在運用產業聚落的外部性經濟優勢提高生產力,也在利用這些知識的流動創造一個具有可塑性的生產過程。集體標竿/collective benchmarking效應便是這種生產過程可塑性的表現。當大量的資本透過不同的管道投注向同一個知識技術時,一方面是在開創龐大的競爭環境,減少壟斷,這在另一方面也是降低了該生產過程對於變化的自我壓抑;既然旁邊一堆的競爭者,每個生產者手上的生產優勢都無法取得足夠的市場,那種吃飽喝足所產生的怠惰就跟著煙消雲散。不知情的人常會對於園區裡對任何小突破汲汲營營衝破頭的模樣感到不解,但一大群的公司在衝破頭的時候,整個生產體系往往可以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發生巨幅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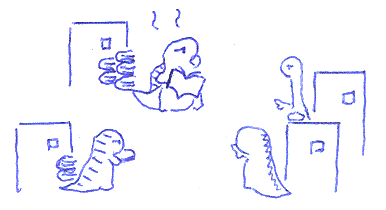
而這種在學術界稱之為『視野』、產業界稱之為『標竿』的方向,也畫下了知識技術的範圍。立竿見影的影子範圍絕對不大,除非頂上的太陽不夠高。Community of practice的創造,經過通訊技術革命後,展現出來的擴張能力比起世襲制的手工業傳承制度還相去不遠。我在分生所某教授的實驗室呆了一年,基本上現在出來和一般的生科系畢業大學生,不論是在手上或是在腦袋瓜裡,都沒什麼兩樣。這種特質,和黑珍珠蓮霧的例子差不多吧!
二、 意見討論
經濟學新制度學派,從交易成本來討論經濟學,我覺得在相當的程度上,他們也必須面對這種知識特性,來論述他們對於組織特性的分析。
換句話說,不僅僅是在生產過程的產業聚落,這種知識流動的特性,也成為限制交易制度變化、交易成本改變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我雖然還尚未閱讀完畢布勞岱爾的<十五到十八世紀 物質、文明與資本主義>三卷,但是前兩本的大歷史觀查,布勞岱爾也間接的與這種知識流動特性產生了對話:布勞岱爾觀察到的歷史經濟演變,他的發現是在交換過程無法達到地理性的聚集與某種一致性的時候,資本主義往往無法進入那些領域產生巨幅的影響,包括交通技術與交換制度,我們淺顯的認為最容易被資本家看上有利可圖的部分;在工業革命產生的同時,整個歐洲社會在許多許多的方面都還保持在傳統的動態上。這是不是在告訴我們說,唯有在大公司都把辦公室搬到同一棟辦公大樓時,交易成本才可能開創新局面;是不是華爾街、西門町,都算是某種型態的交易聚落,和『產業聚落』有一樣的知識動態在維繫他們的存在與建立他們的優勢?我覺得答案已經很明顯了。
區域經濟延伸出來的知識動態和技術流動的觀念,旨在澄清科學與技術在生產交換中的面貌和其本有的特性,對我而言這看似解答了不少的問題,可以用來穿鑿附會的引用到包括新制度經濟學、歷史經濟學、技術社會學與後工業社會理論等等、我感覺在之間連結著的共同命題:技術、知識經濟、組織和管理。
但是另外,如果我們以這個知識動態的理論為出發點,那麼通訊科技的進步,既然並沒有辦法消除知識技術動態的邊界,那這些進步又對知識與科技本身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會是『沒那麼嚴重啦!』抑或是反而影響到更深層的面向?在將來我進行資訊社會學的討論,這會是給我的一個很重要的新出發點。
Dinosaurs 2003/6/4
最近如同上次跟老師面談時說的,我正在考古,瘋狂的從兩年前經濟社會學一課的講義裡研究古典經濟學汲取粗慥的觀念;加上最近和姜俊廷同學常常在討論經濟所劉瑞華所開的『歷史經濟學』一課,與劉老師當時的笑話:他每次講歷史講一講,就會上黑板寫一遍『生產』與『交換』,作為討論背後的主幹,他學期末又上去寫這兩個詞時,自己打趣的說:「下次應該做一張這兩個詞的投影片才對……」突然間,今天冷清的討論課裡,我決定從這個角度提出一點自己對『區域經濟』的論見。
誠如上星期的課堂,老師『迴避』掉了姜俊廷同學提出從市集為出發點的『降低交易成本』理論,將主題濃縮在『生產』面的區域經濟討論。我相信這是因為當時討論的重點是在矽谷與竹科在高科技生產的知識交換『氛圍』,所以要是論及市場行為,實在是非常容易偏離這個主題。
但是我一方面在注意的不僅僅是市集,還有一個是港口。最近我想了一想,覺得當前討論科技產業聚落時講的許多、甚至是『區域經濟』裡最關鍵的知識交換氛圍,我都覺得其實在交換面的這些例子都可以展現出來。譬如說港口,除了基本的先天地理條件,港口的形成往往也是像科學園區一樣的從基本的外在利基與當地人文的某種『氛圍』所構成。港口的興盛,往往不只是地理上的條件所構成,也要配合著當地不同的民情與表現出來的營運風格所展現他們的特性,並且隨著規模擴大時容納的新因素而轉變。尤其以香港這一百年來的歷史來說,我覺得那種展現出來的動態,似乎和矽谷、竹科展現的動態有許多不是很容易察覺的相似面貌。
我希望能從最關鍵的因素:知識交換來簡述我的想法。即使是大航海時代的港口,商人的聚集也絕對會有類似Marshall觀察基爾特、與我們觀察矽谷所看見的那種知識交換的動態,而且相當性的也會有保持在高科技產業裡針對生產過程產生的技術知識交換這種型態。例如大航海時代或之前,帆船的航海技術進步與地理大發現所必須的地理和天氣、各地的商業情形,在一些集中性的商港我相信應該也會有和矽谷類似的知識交換模式,和他們的環境、人文這些氛圍息息相關。
如果討論成功的高科技園區,那我們能討論與觀察的對象就只有兩個;而要是以Marshall為基準,我們大概也只能放眼於『生產過程』中的產業區域經濟。我在想的大問題是,如果改成看『交換過程』的區域經濟,例如姜俊廷提的市集、和大都會、港口等等,我們在討論中馬上會想到的就是上海、廣州與香港從清末到今天的歷史面貌轉變,有著最關鍵性的政治因素在上,徹頭徹尾的影響著他們的發展力。如果『生產過程』與『交換過程』所展現的區域經濟特性是可以相比的,那是否類似政治因素的龐大外在條件,不只是畫地、提供水電等等的成本投資、而是更特殊的一些或好或壞的投注,去構成像矽谷與竹科的氛圍?我覺得從目前以兩個園區、和Marshall展開的取樣與討論,並不是很容易看見這種可以從外在控制的條件、改變區域『氛圍』的力量,如果這種力量是存在的,而且可以和『交換過程』區域經濟的那種力量是可以互相比擬的。這也就是我後來問助教的問題:究竟當提出『氛圍』的時候,是指一種內建在該區域的一種特性,還是一種包圍在該區域外、囊括該區域的一種環境特性?
我以為這若是可以討論的問題,將會是發展討論一些新興科技園區建構過程的可行性的一條出路。
而回到『生產過程』區域經濟的特性,我也在討論中提出過一個觀點,僅供參考。
生產過程從Smith的分工理論開始,如果以公司為單位,Smith可能以為每個過程都有一個獨立的公司來操作,於是從上游到下游,以價格機制為自由資訊交換指標產生的分工溝通就可以運作。顯然從壟斷傾向的市場經濟來看,那種分工的情形並不容易發生。因為一旦中間某個過程產生了壟斷,該處的公司就會立刻展開支配,比如說某家公司掌握著大半的汽車市場,指定與他合作的獨立廠商便成了其他汽車相關產業的強大限制,生產車胎、車窗、車殼、引擎等各種零件的小公司,能與被該公司指定合作的就生存,其他的幾乎只有死路一條。福特主義就是應運這種情形而產生,既然單位被拆開後產生上述的現象,結果只會造成技術進步的障礙,許多其他小公司的新技術反而會被這種壟斷所排斥,那不如把整個分工納入一個公司的生產體系下,進行內部性的資訊交換以克服這種困擾。
我覺得區域經濟在某一方面,展現了突破這種邊界的力量。例如竹科與矽谷面對的高科技產業,展現出來的力量就是分工、代工、合作與競爭並存產生的整體競爭力。在其中,生產過程中每個環節都是被拆解的、可以獨立運作的,所以每個小廠商,都可以針對每個環節取得發展新技術的資本與市場。以我的語言來說:「打破一個公司、一條生產線的界線,生產過程的每個環節,都可以以獨立小公司的型態,敞開的面對自由市場經濟,以及被這種區域經濟給平等化。」既然沒有一個環節可以壟斷整個生產過程,所以各個公司之間,必須不停的展開策略聯盟與知識交換,也給予每個環節獨立的發展空間,加速科技的進步。